陈安民:“历史学家应该认真研究和收集文献”
刘知几在《史通》卷五中,专门设“采撰”一章,探讨历史写作活动中史料的收集与选取。但他虽以“采撰”为章名,却未在本章正文中或《史通》中提及。这一概念在《史通》其他篇章中均有使用。这不同于“直写”、“间接写”、“记事”等,甚至比“叙述”更不常见。刘知几称他采撰文字,秉持“实录”原则。 “以史为本,严以律己,以史为章 ...
那么,何谓“采撰”?“采撰”篇虽无明确定义,但篇章内容结构清晰,问题明确。按照蒲启隆通俗本《史通史》的段落划分,第一段正面阐述了明代学者郭孔彦所说的“采撰宜广,驳斥宜有选择性”的观点,重点强调“史官应认真审阅、搜集文献”。若细究其主旨,大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一是强调史料是史著的基础;二是强调史料的选取是历史写作的重要环节;三是注重考证事实,获得可靠的史实。
《采传》篇中反复强调的“采传”核心思想,是司马迁等人继承下来的,之后又继续发展起来的,在史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影响范围比较有限;在表达历史写作中收集史料的过程时,他本人在文中就使用了“采”和“采摭”等字,使用频率比较高。
历史名著的几个典型特征
据现代统计,《史通》所引书多达345部。再看《古今正史》篇,可见能称得上史学巨著的书有很多,但《蔡传》篇被奉为正典,而《左传》篇则只有《史记》、《汉书》、《史记》三部。正如刘知几在《探精要》篇中所说:“明月之珠,不能无瑕疵,夜光之玉,不能无瑕疵,故作者著书,或有病倦怠。”即使对于这三部书,本篇及其他篇章中也有许多以编撰标准为依据的批评,赞扬未必正确,批评未必恰当,分析其侧重点和批评之处,可以揭示编撰标准,成就一部史学巨著的几个典型特征。
第一,历史名著的本质,在于呈现事实的真相。既然被称为历史名著,核心要求应该是真实可靠的史料及其所承载的史实。正面方面凸显了心胸宽广、怀疑精神的典范,反面则批判了各家之谬,这显然是想将历史著作与经书、文学著作区别开来。文章应“皆真信实”,不“以言点缀”,这样才能“去邪取正,去华取真”,只有记录边疆的人事风俗,才能流传后世,有“此足见文字之功大,岂可与诗文之功相比”之说,明确地赋予了历史著作不同于文学著作承载史实的功能。 《古今正史》篇中说:“经书成书,传于弟子,弟子离去,各持己见。丘明恐真谛失传,遂依原事立传,以示孔子不以空话解释经书。《春秋》批评当时的君臣,事实尽在传中。”这段话,是延续《史记·十二王本纪》所说,也凸显了史书与经书的“本事”与“事实”的区别。其实,这正是《采写》篇中陈述“丘明受经而撰传,广及列国”思想脉络。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收集各个“列国”、各种类型的可信史料。
第二刘知幾史通中的采撰到底是什么?为何引发如此多的争议?,广泛收集、编撰史料。刘知几在谈到《左传》、《史记》、《汉书》的成功时,指出:“当时有周至、晋城、郑舒、楚武,我若单凭陆策,单请教孔子,哪能如此博学多识、阅历丰富?”司马迁的《史记》取材于《史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至于班固的《汉书》,则与太史完全一致。自太初以来,又引刘氏《新续》、《说苑》、《齐略》。此是时之雅言,无邪无邪之意,故能信守一时,名扬千古。”这段话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一是强调他们在史料搜集、编撰上呈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来源具有“国”“地”“类”的广度,可信度也都是“当代雅言,无邪无奇”。二是刘知几所例,强调可靠的文献资料,这与《搜集撰文》篇末对司马迁、孙盛游记、访谈取证的批评是一致的。来源“采自《左传》、《国语》,删自《世本》、《战国策》,以楚汉时事为准”,比《搜集撰文》篇更加细致,更加有区别,更能彰显古今的联系。三是如何看待以《全通太史》为代表的前代权威的问题。 如今人们普遍认为,《汉书》与《史记》重叠部分用旧文较多,且有许多重要史料被引用,郑樵对史料的补充和修订,自称“窃取乾隆全书”的说法,确实过于偏激。对历史的重写,在史料方面处理好后世史书与现存著述的关系,是《汉书》成功之处,值得借鉴之处。
第三,他虽然缺乏疑义,但并不消极,积极地寻求补充正典旧史的不足。刘知几在赞扬马班著述广泛、文采风雅、可靠史实之后,开始追溯“中古”以来“引书错误”的根源。他把神话、寓言、预言等纳入历史,视为“谬误”、“异端”、“假新事”。近代学者张舜晖曾有意把刘知几对马班典范的论述与引书错误联系起来,指出司马迁“古事必有据,不知则略,不拘谬谬,足见其搜集、编撰之慎重”。高远深远,言辞可敬,空洞无物。故吾要搜集、利用杂书,难分清清正与驳斥。 因此,我肯定刘知几的判断“不苛刻”。刘知几解释了司马迁为何将伯益、叔齐置于列传之首2023年管家婆精准一肖,并指出:“史是书,有实事则记,无实事则略。”古事无书证,故无据可查。疑虑可以理解,但好史家不置可否。若能调查、记录相关民间传闻,亦能揭露古史的踪迹。对于现代事件,采访旧人,则极为必要,也更具可能性。
对此,《史记》作者以广泛的游历和探索,展示了田野调查对提升名著的宝贵价值。现代学者程千帆在评论“采撰”篇时,系统地整理了司马迁本人所提及的史料来源,除“取材于简牍和书籍”外,还有“取材于当时人所说”、“取材于亲临所见”、“取材于亲见而传述”等。 面对这样的现实,刘知几在《采写》一章的结尾认为:“观孔子作《史记》,自殷周以来,采世家;安国作《阳丘》、梁、夷旧事,访旧人。若取尧之卑言2023管家婆必开一肖一码,印于简帛之上,欲与五经、三史争,亦难矣。”《史记》本身就包含《史记》,刘知几的说法本身就有逻辑上的错误。但他这种一味崇尚文学、轻视名誉的态度,却受到吕思勉、程千帆、张舜徽等《史通》注家的一致否定。刘知几的不当批评,恰恰从反面表明了司马迁对各方面都同等重视。《史记》成功的秘诀 “史学家”就是对这类文献的收集、撰写,并辅以调查和口口相传。
历史著作中广泛存在的史料,是史学家主观努力寻找的结果,但也很大程度上受到时代条件的创造和制约。刘知几在《探索》、《反省》、《古今官史》等文章中明确指出: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如从割据到统一的过渡2023的新澳门开奖结果查询,从告示制度到建立严格的史料收藏制度,交通条件的改善等,都对史学家撰写的史料的收集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历史博物馆受到的批评之一,就是史料收藏体系的崩溃。纵观历代史料的收集和发行,刘知几以理论概括的方式提出了这一命题:“吾以为近史杂乱,若实,亦如古今史。当然,史料的增多,既是广泛收集的机遇,也是审查和选择的挑战。”
(作者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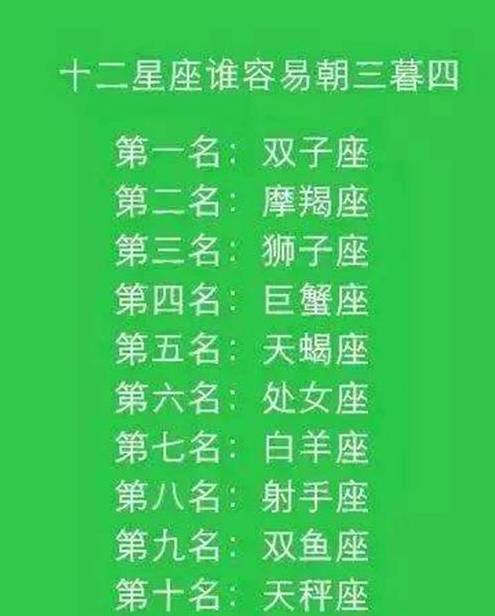





发表评论